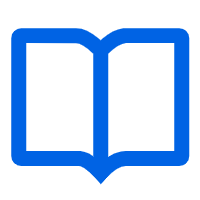骖是什么生肖?
《说文》:“骖,车旁之马也” 段注原文:“古者乘舆,左右必须马各二,谓之骖。如《周礼·司仪》:‘设其骖。’《夏官·校人》:‘凡厩,右之马谓之骖。’今俗所谓驾三马者,非古之意也。” 所以,骖是古时驾车的左右两边各两匹马。 段注原文中已经解释了,不是指一上车就两边各两匹。而是说“左之马”“右之马”“前之马”“后之马”。其中,“左之马”“右之马”指的是随从的护卫之马。(因为古时礼仪,天子出行时,左边护卫马队要大于右边) “前之马”“后之马”,是指前面引路、后面殿后的马。 根据这些解释,我们再来看“巳午未申”四地支所代表的时间段,就知道为什么分别是马,羊,羊,猴了。
古人一天的时间划分与现在不同,他们是以十二个时辰来计算时间的。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。而每个时辰分为初、正两个时段。 子丑寅卯四个时辰,对应今天深夜一点到三点,这个时间段正好属于“夜半”时间,也就是今天的午夜时分。 四地支中,亥子丑对应着猪鼠牛,当然这仅仅是按地支排序来说的。如果结合十二时辰,那么就是“夜半”时间点之后的“丑时时分”,也就是凌晨一到三点。在这个时间里,自然属于“牛”的阶段。所以,“已午未申”中的“未”代表羊,就是这个道理。 因为古代建筑都是以木结构为主,白天夜晚是没有明显区分的。所以,“昼“夜概念也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区分。
在汉代,人们把白天的十二时辰分为“晨”和“昏”。而“黄昏”这个词很形象地反映出来了“夕阳西下”的画面,可以想象,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“昏”的时候,自然属于“犬”(黄昏即日落,属狗)。 而“黎明”则是第二个阶段,这时天还没亮,属于“鸡鸣”之时,故为“酉”。 就这样,我们找到了“巳午未申”各自的对应动物。但是,这是不是意味着十二生肖就确定下来了呢? 并不是!!!
虽然古人把十二生肖放在十二地支之后作为记年之物,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顺序就是现在的顺序。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就提到“秦灭六国,统一天下,以为秦纪六十年,数起于始皇元年,卒于秦始皇二十六年。二年,天子始立正月,岁首,众庶人君,皆贺正月,万民便乐,故正月为一元。十六日,月宿在寅。”
在这段记载里,很明显提到了“寅”这个地支,以及根据“正月一元”推算出来的“寅月”。并且指出“十月”属“亥”。而“亥”正是生肖猪。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。那就是上古时期,“子丑寅卯”可能并非按照顺序排列。否则,“十月”怎么可能是亥月?
《周礼春官宗伯·牧师》中有:掌牧师之政令,以牧师万民:辨六兽之物而掌其政任,以扰治邦国。凡共祀宗庙,是其牺牲牷物。辨其禴、禘、蒸、狩之义,以诏王特牲。以知六畜疗斮之禁,辨其物叙之纯殽,以共王膳。掌建国之神位,右社稷,左宗庙。右尊尚肝,左尊尚心,心肝,牲之上下贵也,故尊尚焉。
郑玄注“辨六兽之物”曰:“马牛羊曰大兽,与其小谓之六。”马牛羊曰大兽,郑玄认为,大兽和与其相类的小兽叫做六兽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中卷十八“兽”字下解释说:“兽者,顺也……《周礼》曰:马牛羊曰大兽也。”
由此推断,郑玄解释的六兽之物里的“与其小”,就是指与大兽马牛羊之类的小动物,即与马类、牛类、羊类相类的小动物。也就是《易传》所谓乾“为龙、为马、为玄黄”。“为龙”意指乾具备龙的属性,即具有龙的特征,而不是说乾就是龙。《说文解字》中:“龙,鳞虫之长。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短能长。春分而登天。秋分而潜渊”,“马,怒也,武也……象头耳足之形”,“玄”为“幽远也……黑而有赤色”、“黄,地之色也……天玄而地黄”。这说明龙与马具有共同的特征和属性,二者是同类物体。只不过马是现实世界里的具体的可见的物体,可以“名”之;龙是超越现实世界里的抽象的不可见的物体,是神化、幻想、夸张了的马,“不可以名,故谓之龙。”“玄黄”是龙、马的共同颜色,是天和地的五行“生”色。所以龙、马、玄黄是同质异体的动物,是三位一体的。
那么“马牛羊”和“马牛牧”之间、“马”和“牧”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呢?“牧”字在金文中,“从牛从林”,意为牛在树林中活动。这里“林”字应释读为“物”,指树木,“从牛从林”即为动物牛在树林中活动之貌。“牧”字甲骨文作“”,上面是三个“木”字构成的“”,与“林”字相同,下面是“牛”字。与金文同。“牧”字小篆作“”。本从攴,牧省作“”不从“攴”的,“牧”字甲文是“以牛从林”。与本义“放牧牲畜”和“放牧牛羊”相吻合,“牧”在金文就是“牛”在“林”即“物(wù)”中活动。“牧”字的本义也是“养牛羊之谓”,甲骨文的“牧”,上面是一个“林”字,下面是一个“牛”字,合起来是一只牛在树林中活动。金文也与此相同,由此推断,甲骨文、金文的“牧”本是一个牛在林中放牧之貌。“牧”就是指“养护、放牧”的意思。“牛羊”之兽(即“马牛羊”之中的牛、羊,而不是指“马牛牧”中的马、牛和后面的牧)在“林”中放牧,所以金文的“牧”从牛从林。
“马牛牧”不是指马、牛、牧这三种动物,而是指牛(马)在林(物)中活动之貌。“牧”字在《说文》中从“攴”,甲、金“牧”字无“攴”,今本《说文》从“攴”是后人解释时加的形旁表声。因为《周礼•春官•大祝》中有“掌六辞:一曰和辞,二曰诰辞,三曰祀辞,四曰赐告,五曰令,六曰禁”,大祝掌国事,而大祝掌六辞,故而从“言”,“言、言、言、、诰”皆为“言”字头。《周礼•春官•大史》